如果说法国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可能大多数人不无刻板的第一印象会是苏菲·玛索、阿兰·德龙,或者时尚产业的香衣鬓影、凡尔赛宫的浮华往事……然而,法国还有另外一重“看脸的社会”。
6月26日,欧洲人权法院(CEDH)作出判决:法国政府因对本国公民实施歧视性的身份检查、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而被判败诉。这一判决引发维权团体的欢呼,被称为“历史性的胜利”,同时也将法国宪警部门多年来一直备受诟病的“看脸查人”问题再次带回到聚光灯下。
所谓“看脸查人”(contrôle au faciès,亦译为“貌相检查”),指的是法国警察和宪兵在公共场所的日常执勤中有权查验公民身份,但其遴选检查对象的标准不是基于对方具体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危害程度,而是基于外貌特征。虽然笼统而言,这种外貌特征的外延可以相当广泛(例如性别、身体残疾、政治立场符号等),但在实际运作中,主要集中在种族、宗教或国籍上(无论是真实还是推定的)。正因如此,“看脸查人”一直被指责具有明显的歧视、尤其是种族歧视嫌疑。
“看脸查人”引发的争议,在法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宗教极端分子频频制造恐怖袭击、街区治安问题并无改善、涉毒及帮派问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宪警部门承担着巨大的安保压力。在重点区域进行身份盘查,成为案发前消除隐患、案发后追查嫌犯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批评者看来,这种措施不仅有效性值得怀疑,而且有饮鸩止渴之嫌,无形中反而加剧了警民对立。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固然构成了一种警告,但在“看脸查人”问题上其实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方。以此为镜鉴的意义,毋宁说在于:一方面,真正的法治原则拒绝对公民的人身和行动自由进行大规模的、专断的限制,哪怕这种限制以冠冕堂皇的公共利益为理由;另一方面,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出发点,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或明或暗的区别对待(甚至歧视),虽然可能会暂时清除表层不稳定因素,但难以消弭深层根源,甚至可能会遭遇反噬。
“一胜五败”的法院判决
2025年6月的这份判决,其实是一场漫长司法诉讼的尾声。在欧洲人权法院,该案被统称为“塞迪等人诉法国”(Seydi et autres c. France),案中共有6名原告,均为非裔或北非裔,自认为在2011-2012年间成为警察“看脸查人”的受害者,其居住地分布在巴黎郊区、里昂郊区、北部的鲁贝(Roubaix)、东部的贝桑松(Besançon)、南部的马赛等多地,换句话说,可以近似地被看作是法国全境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2012年3月,“塞迪等人诉法国”一案中的六名原告(事实上在初始阶段人数远不止六人)致函内政部,要求告知他们被警察检查的原因,而内政部虽然回复称会将相关情况反馈给警方,但随后杳无下文。于是政府被告上法院,要求就“歧视性”的身份检查承担责任。2013年10月,巴黎地方法院驳回了相关诉讼请求。在随后的上诉程序中,上诉法院也维持原判。于是,在诉诸国内司法救济未果之后,六人上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然而在6月26日的判决中,最终只有来自贝桑松的图伊勒(Karim Touil)一人的诉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其他五人均遭遇失败。
相比同案其他原告,图伊勒的案情相对而言最为特殊:他是唯一一个短时间内接受多次检查(10天里连续三次)、所遭受对待也最恶劣的人。
2011年11月22日,图伊勒和两名同伴在贝桑松市中心被警察拦下,接受搜身盘查并出示了身份证件。十天之后的12月1日,他在街上和两名同伴闲坐时,看到有警察靠近,用暗语对同伴说,“看,22(意指警察)来了”,警察听到这话反呛说:“来吧,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自作聪明的”,还说“我们知道你们这些街区暗号”。于是图伊勒再次被搜身检查。两个小时之后,他和另外五名同伴(其中两人第二次盘查时也一同被查)在市政府门口又被警察盘查。这一次,一名警察颇为恶意地对图伊勒说,“你太胖了,得减肥,去运动一下。”随后双方对立情绪升级,在发生口角之后,图伊勒被一名警察扇了一巴掌,被带上警车并遭拘捕。
在寻求国内司法救济的过程中,上诉法院承认图伊勒遭受了口头和身体上的不公对待,但同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不公对待和种族歧视相关,也无法让人认为其种族是引发身份检查的原因。
然而,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图伊勒的情况和其他几人都有不同:第一,图伊勒提交了一份统计数据,证明他所属的群体被警方“过度盘查”;第二,他在十天内遭遇三次检查,后两次甚至发生在同一天里;第三,针对第一次检查,政府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法律依据;第四,针对第二次检查,虽然政府方面提出贝桑松检方曾颁令在特定时段调查某些罪行,但这次检查并没有发生在这一特定时段内;第五,在第三次检查中,警方曾对他有过侮辱和暴力行为。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系列“严重、确切、一致”的证据,足以构成推定——即警方在身份检查中具有歧视性;于是,举证责任转移给政府,而后者并没有针对这三次检查中的任何一次提供客观且合理的说明。换言之,原告成功地确立了对其检查具有歧视性的推定,而作为被告的政府未能有效反驳,于是这种歧视性推定可以被视为成立。由此,法国政府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禁止歧视)和第8条(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规定,因此被宣告败诉,并应当向图伊勒支付3000欧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告要求5000欧元)。
打折扣的“历史性胜利”
判决作出后,图伊勒的律师阿舒尔(Slim Ben Achour)兴奋地表示,这是一次“巨大胜利”,“因为法国第一次在欧洲层面被判定有种族歧视行为存在”。
“看脸查人”问题虽然在法国频频成为焦点话题、但作为行政分支的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有这种做法,其原因不难理解,毕竟宪警部队直接听命于内政部,除非过错明显到无法公然袒护的地步,否则政府必然要坚决维护宪警部队的权威,加上警察工会的强势作风,导致相关争议屡屡成为针尖对麦芒式的对抗。2020年“黄马甲”示威期间一名黑人音乐家遭受警察殴打之后,总统马克龙也不得不承认“非白人会受到更多检查”,警察工会对此不仅大为光火,甚至有底气通过拒绝执行身份检查这样的“撂挑子”行为来施加压力。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9日,法国巴黎,巴黎北站,法国警方人员执勤。
不过在司法领域,这块坚冰正在被逐渐打破。在近年来的多起判决中,法国国内不同法院陆续承认宪警执法中存在歧视性的“看脸查人”问题:2016年11月,最高法院在三起身份检查案件中裁定政府相关行为具有歧视性,导致“严重过失”违法;2021年6月,巴黎上诉法院认定警察在2018年12月的一次身份检查行动中犯有“重大过失”,具有歧视性;2023年10月,最高行政法院承认警方执法中的确存在歧视性的身份检查,对当事人造成了有害影响,而且认为这并不是“孤立”事件。
因此可以说,此次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石破天惊的转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法国国内司法意见合乎逻辑的发展,它的真正独特之处不在于法国政府遭遇败诉,而是在欧洲层面上败诉,由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更大的法律和道义压力。
但如果仔细审视这一案件,不难发现,除了在欧洲层面上有所突破外,所谓“历史性胜利”也打了相当大的折扣。一方面,除图伊勒之外,其他五名原告的诉求均被欧洲人权法院驳回,这意味着不那么具有戏剧性冲突的案情,即便穷尽了所有司法救济手段,也很难讨到满意的说法;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坚决否认现行身份检查体制存在“系统缺陷”,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法国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并没有显示出“结构性缺陷”:虽然当事人在初审和上诉的国内司法救济途径中屡屡遭受挫败,但是否存在“结构性缺陷”并不以是否能满足原告期望作为判断标准,而是看司法和行政体系是否提供了足够完备与合理的救济渠道。
除了“个别否定、总体肯定”的判决外,在技术层面,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律论证也不无可商榷之处。针对图伊勒的判决,欧洲人权法院的合议庭以6比1的多数作出判决,而来自法国的法官穆鲁-维克斯特罗姆(Stéphanie Mourou-Vikström)发表了唯一一份异议意见。尽管她的意见处于绝对少数地位,但其中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认真对待。
简而言之,穆鲁-维克斯特罗姆认为,在判断身份检查是否存在歧视时,法院的首要考虑因素应当是当事人是否受到了宪警方面的“区别对待”,而且在“塞迪等人诉法国”一案的其他部分当中,法院也是这样做的;但在针对图伊勒的考量中,法院却没能坚持这一点,而是强调各种因素的叠加组合,并将其作为确认证据效力的主要考虑因素。换句话说,多数意见并没有找到图伊勒遭受所谓“歧视”的实质证据,而是把一系列对侵害当事人的情节打包起来考虑,并通过举证责任的配置、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但这些情节实际上和图伊勒属于少数族裔并没有任何关联。
穆鲁-维克斯特罗姆警告,图伊勒案并不只是个例,它可能会给一个新的证据模式敞开大门,即把不同因素组合起来加以考虑,而“区别对待”这一核心要素反而不再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进行跨语境类比的话,欧洲人权法院针对图伊勒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别对待,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语境中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尽管在实质层面上,图伊勒方面提交的证据并没有一锤定音的“法律效果”,但鉴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尤其是警察的口头和身体暴力,导致如果忽视这种暴力、将图伊勒和其他人等量齐观,一味要求证明“歧视”的证据,会造成显然不公的结果,因此法院用推定方式,为这种“社会效果”的正义寻找出口。
解法何在?
法国的“看脸查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其庞大数量。法国审计法院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以最近的2021年数据来看(尽管仍不够完整详尽),全年范围内宪兵进行了大约2000万人次的身份盘查,警察进行了大约2700万次身份盘查,二者合计总数高达4700万次。
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此类盘查数量庞大,但法国并不允许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身份盘查。在2015年恐袭之后的风声鹤唳背景下,法国议会曾修订紧急状态法律,授权各省省长无需基于特定威胁、就可以下令检查行人、行李和车辆。但宪法委员会在2017年12月的一份裁决中宣布该法律违宪,并强调,立法者必须在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虽然公权力可以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特别措施,但“普遍”和“专断”的身份检查,和尊重个人行动自由和保护隐私权的原则背道而驰。
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78-2条的规定,除了司法警察侦查案件、边境地区、跨国交通、海外领地等特殊情形外,日常的身份检查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检方为了调查违法犯罪行为而提出书面要求,由宪警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内,可以对任何人进行盘查;二是宪警人员为“预防公共秩序、特别是人身及财产安全受到侵害”,可以对任何人进行盘查。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针对不同人群的“区别对待”往往难以避免,因为检方会根据已经发生的案情来启动调查,而案情中经常已经涉及嫌疑人的笼统身份,例如在“塞迪等人诉法国”一案中,迪亚·阿布迪拉希(Dia Abdillahi)被盘查前有“两名北非裔人员”在当地涉案,塞迪被盘查前有“两名非裔年轻黑人”涉案,因此宪警在检索目标时必然会侧重于此类群体,因此更容易被指责有种族歧视嫌疑。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主要集中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场合、以及治安不佳的所谓“敏感街区”,其语焉不详的措辞导致了很大的解释空间,同时意味着赋予执法人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国警察监察总署(IGPN)2023年的一份报告强调,在“敏感街区”或者少数族裔聚居区域,年轻人扎堆聚集是一种客观现实,不可能因为忌惮于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就让警察专门去针对白人去检查来刻意寻求平衡。欧洲人权法院在此次判决中也承认,法院“充分意识到警员所面临的困难——他们在并不必然具有明确内部指示的情况下,需要非常迅速地判断公共秩序或安全是否面临威胁”。
然而,每年数千万次的执法行动始终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缺乏可靠的跟进措施,导致政府在面对法律挑战时,很难在事实层面作出有力辩解。从“塞迪等人诉法国案”中不难发现,由于既未配备摄像头也缺少书面记录,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方面未能提供有效的反对证据。在法院判决中,几乎每一例的事实部分最后都写道——“警方版本未被记录,或至少未被通报给法院”。
面对各方均难以满意的困境,解法之一是为被检查者开具书面收据,并通过这些书面收据汇总身份检查执行情况的全貌(这也是左派政党和人权组织多次要求的措施)。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与身份检查相伴随的详细记录(包含族裔和国籍等信息),进而建立一个具有“可追溯性”的数据库,才能从中明确看出这种身份检查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

当地时间2025年6月18日,法国巴黎,行人抵达巴黎火车北站。
但这种解法至少面临两个障碍:一是政府方面无意配合,认为实施起来面临很大困难,因为此类检查的数量庞大,如果每次都要给当事人开具收据,并会大大加重宪警的文牍工作负担,这和近年来的“去文牍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二是即便通过书面收据建立数据库,又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1978年的一项法律明确禁止处理事关种族和族裔的个人特征数据(这也是今天法国少数族裔占人口比例的数据始终缺乏权威来源的原因)。
解法之二是让宪警执勤时佩戴并展示可追溯其身份的号码(RIO,相当于中国的警号),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地位相对平等,并在投诉时有据可循,但在实际操作中,宪警成员经常不履行这一职责,或者故意将号码放在不显著的位置上,导致当事人难以指认。
解法之三、同时也是眼下最为现实的解决手段,是为宪警部队普遍配备随身摄像头(执法记录仪)。法国内政部从2021年开始为宪警部队普及配备摄像头,到2023年共配备了5.4万台摄像头(其中3.2万用于警察,2.2万用于宪兵)。但要让这一技术手段顺畅地融入执法过程中(例如现阶段无法确保摄像头续航能力覆盖全天执勤、而且宪警执勤时不开启摄像头也并不受处罚),恐怕还需要相当长时间。
意在维稳 反酿敌意
就在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的前两天,法国的人权保护专员(Le Défenseur des droits)于6月24日发布了此前委托民调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相比进行上次同类调查的2016年,法国人曾接受身份盘查的比例大幅增加,有26%的受访者在过去五年中曾被宪警盘查,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16%。具有黑人、阿拉伯人或马格里布(即北非)外貌特征的群体,遇到身份检查的几率平均要比白人高30%,而其中的年轻男性被检查的风险是普通人的四倍,而遭遇搜身等“深入检查”的风险则要高出12倍。
不难发现,在“看脸查人”是否具有歧视性质的问题上,它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发生了脱节,无论各级法院如何在证据层面上斟酌,在社会公众的反馈中,这种区别对待(姑且不说是“歧视”)早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和这种区别对待相伴生的现象是,公众对宪警部门的不信任感乃至敌意也会随之上升,尤其是宪警在检查过程中出现的侮辱和暴力行径,更加剧了当事人的敌对感。根据人权保护专员发表的这份调查结果,当看到宪警在公共道路上执勤时,已经有22%的受访者抱持着不信任感,而如果再遭遇前者作出侮辱等“不专业”行为,这种不信任比例高达61%。
此外,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宪警方面的敌意和歧视有时还通过间接隐讳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塞迪等人诉法国”一案中,迪亚·阿布迪拉希2012年2月在巴黎郊区遭遇检查时,警察看到他证件上的居住地是南法城市马赛,便用一种讽刺性的口吻说,“你在度假?不工作吗?快点去找份工作,因为等萨科齐上台,你就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段话表面上没有一个脏字,但实际上几乎毫不掩饰地反映出法国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即认为许多黑人和阿拉伯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亟须右派政府上台好好“管教”一下。
按照2014年的《内部安全法典》规定(在“塞迪等人诉法国案”事发时尚不存在),宪警在执行任务时应“完全公正无偏私”,对所有人给予“相同的关注和尊重”,在行为和言语中“不应有任何区别对待”,必须使用“您”的尊称,进行身份检查时“不应基于任何生理特征或任何显著标志来确定需要检查的人员”,检查时“不应侵犯被检查者的尊严”,“只要情况允许,搜身检查应在公共视野之外进行”。
但和这种理想境界相反,现实中发生的身份盘查、尤其是有“看脸查人”之嫌的检查往往给当事人带来强烈的负面冲击。在公共场合被拦截盘查,本身就会导致“凭什么是我”的被针对性;宪警不使用尊称、乃至使用街头粗俗语言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例如人潮汹涌的车站大厅里)公开搜身也屡见不鲜,这无疑会给当事人造成强烈屈辱感,并进而形成对宪警部门乃至整个公权力机构的敌意。
在这里,大规模的“看脸查人”展现出它真正的危险之处,即某种“自证预言”的效应——从“看着就不像好人”的潜意识出发,以专断甚至粗暴的盘查手段为催化剂,通过刺激当事人的屈辱感和怨恨感,反而加剧了这种异己心态,并成为更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心态根源。如果说2005年的巴黎郊区骚乱已经逐渐被人淡忘的话,2023年同样发生在巴黎郊区、因身份盘查而引发的“纳赫尔之死”迅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骚乱,再次暴露出同样的痼疾:持续多年的身份盘查措施,或许可以消除某些不安定因素,但同时无助于从根本上缓和持续紧绷的警民关系。
既得利益群体的错觉
在这种对抗性机制中,华人无意中成为某种既得利益群体,因为通常而言,东亚和东南亚族群暴力扰乱公共秩序的几率较低(但亦偶有发生,如2017年的刘少尧案),所以较少成为警察盘查的对象。一个旁证是,在“塞迪等人诉法国”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警察盘查塞迪时,后者正和一位泰国朋友同行。塞迪本人出示身份证件后,这名泰国人起初也被要求出示证件,但警察很快改口说算了不需要,于是这种“区别对待”成为塞迪认为构成歧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南亚裔群体遭遇的警惕程度更高。随着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的发生(例如和宗教及部族相关的所谓“名誉杀人”),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群体正越来越成为法国警方关注的目标, 虽然通常认为黑人和阿拉伯人是“看脸查人”的主要受害者,但有警察在匿名接受电视采访时,已经明确把“巴基斯坦人”和上述二者相提并论。
这种细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往往会形成一种心理错觉,将“因为无害所以无视”理解为“因为无涉所以高等”,加上客观而言华人往往成为治安案件的受害者,所以更容易矫枉过正,对本质上属于种族歧视性质的行为安之若素,甚至不无欢迎——殊不知这可能只是没有歧视到自己头上。倘若换一种场合(例如当打击街头卖淫时),华人面孔同样可能沦为某种刻板印象和“看脸查人”的受害者。因此,唯有以“公正无偏私”为根本价值,共同维护“观念水位”不至于下降太多,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身利益。否则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思维大行其道,华人华裔也注定会遭受附带伤害。
结语:中式赛博朋克参照系?
法国社会中的种族平等与融合,本身具有绵长的传统。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用不乏夸张的笔调描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黑人小伙和白人姑娘相拥走进小旅馆,是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的“种族平等”景象,足以让其他欧洲人大为惊骇。而百余年之后,当类似的图景在欧洲已经多多少少变得“正常化”之后,开欧洲风气之先的法国,却在平等和博爱表层之下,仍然深受分殊和歧视的困扰。不同民族和种族在这里“相爱相杀”,彼此勾连、嵌套、亲近、敌视,“看脸查人”只是最凸显的表现之一。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1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特罗卡德罗广场,法国移民法的反对者举行抗议活动。
时至今日,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政治中的左右营垒泾渭分明。左派政党和人权团体对“看脸查人”保持高度警惕和批判性态度,致力于强调“结构性问题”(例如2024年五家人权组织联名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谴责法国的“系统性身份查验歧视”现象),并期待能从根本上解决病灶;右翼则坚定地站在宪警部门的身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树立起权威,寻求所谓“根治”失之天真,缓不济急。众所周知,宪警群体是右派甚至是极右派的天然票仓,对“法律与秩序”的诉求,不仅是宪警群体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右翼的政策主轴之一。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手握枪把的宪警力量,“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容易流于滥权自不待言,而从更广义上说,其实政治光谱上的每一个生态位,都天然地倾向于扩张自己的诉求,无论是“安全”还是“平等”均是如此。但左翼的平等理想,和右翼的权威幻象,二者都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中寻找折中和妥协。司法判例的严正警告是一条边界,现实运作中的可操作性是另一条边界。围绕“看脸查人”的种种争议,远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解决方案。
跳出法国的语境,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在日常生活中,“以貌取人”事实上屡见不鲜,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另一种“以貌取人”不仅正在成为现实,而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面部识别技术日益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形成了另外一种“看脸的社会”。从公共交通检票、闯红灯曝光、到“演唱会追逃”,“脸”正在越来越脱离个人隐私范畴,成为赛博空间里的一种公共资源。从纯粹技术意义上说,这或许会成为未来法国“看脸查人”困境的另一个解法,以“明日的世界”来升级“昨日的世界”:面部识别和行为预测交给街头全景式监控和大数据分析来完成,前线宪警力量根据威胁优先程度进行有效调配,佐之以随身摄像头的不间断直播,以及后方的实时评估与介入,“查人”将更加精准高效、非个人化、非情绪化,一劳永逸地解决“歧视”指控的困扰,或者说,这种指控只能针对算法,而非个人。
只不过,对于法国宪法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黑镜式世界。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看脸查人”漫长诉讼落幕:法国在平等理想和无奈现实间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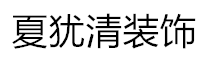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13
京ICP备2025104030号-13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